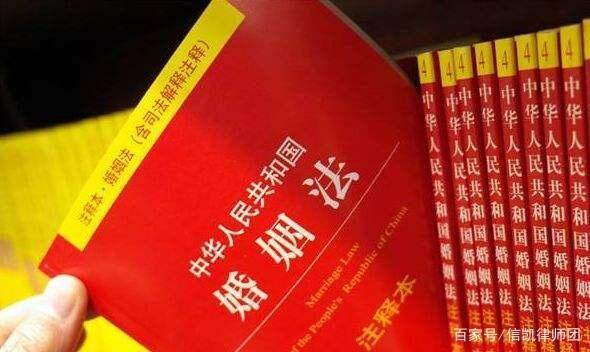序
《史記》曰(一):「齊民無蓋藏。」如淳注曰:「齊,無貴賤,故謂之齊民者,若(二)今言平民(三)也。」
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
蓋神農為耒耜,以利天下;堯命四子「一」,敬授民時;舜命后稷,食(四)為政首;禹制土田,萬國作乂「二」;殷周之盛,詩書所述,要在安民,富而教之。
《管子》曰(五):「一農不耕,民有飢者;一女不織,民有寒者。」「倉廩實,知禮節;衣食足,知榮辱。」丈人曰(六):「四體不勤,五穀不分,孰為夫子?」傳曰(七):「人生在勤,勤則不匱。」古(八)語曰:「力能勝貧,謹能勝禍。」蓋言勤力可以不貧,謹身可以避禍。故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,國以富強;秦孝公用商君,急耕戰之賞,傾奪鄰國而雄諸侯(九)。
《淮南子》曰(十):「聖人不恥身之賤也,愧道之不行也;不憂命之長短,而憂百姓之窮。是故禹為治水,以身解於陽盱之河;湯由苦旱,以身禱於桑林之祭「三」。……神農憔悴,堯瘦,舜黎黑,禹胼胝。由此觀之,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。故自天子以下,至於庶人,四肢不勤,思慮不用,而事治求贍「四」者,未之聞也。」「故田者不強,囷倉不盈;將相不強,功烈「五」不成。」
《仲長子》曰(十一):「天為之時,而我不農,穀亦不可得而取之。青春至焉,時雨降焉,始之耕田,終之簠、簋「六」,惰者釜之,勤者鍾「七」之。矧夫不為,而尚「八」乎食也哉?」《譙子》曰(十二):「朝發而夕異宿「九」,勤則菜盈傾筐。且苟無(十三)羽毛,不織不衣;不能茹草飲水,不耕不食。安可以不自力哉?」
晁錯曰(十四):「聖王在上,而民不凍不飢者,非能耕而食之,織而衣之,為開其資財之道也。……夫寒之於衣,不待輕煖;飢之於食,不待甘旨。飢寒至身,不顧廉恥。一日不再食則飢,終歲不製衣則寒。夫腹飢不得食,體寒不得衣,慈母不能保其子,君亦安能以有民?……夫珠、玉、金、銀,飢不可食,寒不可衣。……粟、米、布、帛,……一日不得而飢寒至。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。」劉陶曰(十五):「民可百年無貨,不可一朝有飢,故食為至急。」陳思王曰(十六):「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「一0」,飢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。千金、尺玉至貴,而不若一食、短褐之惡者,物時有所急也。」誠哉言乎!
神農、倉頡,聖人者也;其於事也,有所不能矣。故趙過始為牛耕「一一」,實勝耒耜之利;蔡倫立意造紙,豈方縑、牘之煩「一二」?且耿壽昌之常平倉「一三」,桑弘羊之均輸法「一四」,益國利民,不朽之術也。諺曰:「智如禹、湯,不如嘗更(十七)。「一五」」是以樊遲「一六」請學稼,孔子答曰:「吾不如老農。」然則聖賢之智,猶有所未達,而況於凡庸者乎?
猗頓「一七」,魯窮士,聞陶朱公富,問術焉。告之曰:「欲速富,畜五牸(十八)。」乃畜牛羊,子息萬計。九真、廬江,不知牛耕,每致困乏。任延「一八」、王景「一九」,乃令鑄作田器,教之墾闢,歲歲開廣,百姓充給。燉煌不曉作耬犁;及種,人牛功力既費,而收穀更少。皇甫隆「二0」乃教作耬犁,所省庸力過半,得穀加五。又燉煌俗,婦女作裙,攣(十九)縮如羊腸,用布一匹。隆又禁改之,所省復不貲。茨充「二一」為桂陽令,俗不種桑,無蠶織絲麻之利,類皆以麻枲頭貯衣「二二」。民惰窳羊主切,少麤「二三」履,足多剖裂血出,盛冬皆然火燎炙。充教民益種桑、柘,養蠶,織履,復令種紵麻「二四」。數年之間,大賴其利,衣履溫暖。今江南知桑蠶織履,皆充之教也。五原土宜麻枲,而俗不知織績;民冬月無衣,積(二十)細草,臥其中,見吏則衣草而出。崔寔「二五」為作紡績、織紝之具以教,民得以免寒苦。安在不教乎?
黃霸「二六」為潁(二一)川,使郵亭、鄉官「二七」,皆畜雞、豚,以贍鰥、寡、貧窮者;及務耕桑,節用,殖財,種樹。鰥、寡、孤、獨,有死無以葬者,鄉部書言,霸具為區處:某所大木,可以為棺;某亭豚子,可以祭。吏往皆如言。襲遂「二八」為渤海,勸民務農桑,令口種一樹(二二)榆,百本「二九」,五十本蔥,一畦韭,家二母彘,五雞(二三)。民有帶持刀劍者,使賣劍買牛,賣刀買犢,曰:「何為帶牛佩犢?」春夏不得不趣田畝,秋冬課「三0」收斂,益蓄果實、菱、芡。吏民皆富實。召信臣「三一」為南陽,好為民興利,務在富之。躬勸農耕,出入阡陌,止舍離鄉亭「三二」,稀有安居。時行視郡中水泉,開通溝瀆,起水門、提閼「三三」,凡數十處,以廣溉灌,民得其利,蓄積有餘。禁止嫁娶送終奢靡,務出於儉約。郡中莫不耕稼力田。吏民親愛信臣,號曰「召父」。僮种(二四)「三四」為不其令,率民養一豬,雌雞四頭,以供祭祀,死買棺木。顏斐「三五」為京兆,乃令整阡陌,樹桑果;又課以閑月取材,使得轉相教匠「三六」作車;又課民無牛者,令畜豬,投貴時賣,以買牛。始者民以為煩,一二年間,家有丁「三七」車、大牛,整頓豐足。王丹「三八」家累千金,好施與,周人之急。每歲時農收後,察其強力收多者,輒歷載酒肴,從而勞之,便於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,因留其餘肴而去;其惰者,獨不見勞,各自恥不能致丹,其後無不力田者,聚落以至殷富。杜畿「三九」為河東,課民畜牸(二五)牛、草馬「四0」,下逮雞、豚,皆有章程,家家豐實。此等豈好為煩擾而輕費損哉?蓋以庸人之性,率之則自力,縱之則惰窳耳。
故《仲長子》曰:「叢林之下,為倉庾之坻「四一」;魚鱉之堀「四二」,為耕稼之場者,此君長所用心也。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,鄭、白「四三」成而關中無飢年。蓋食魚鱉而藪澤之形可見,觀草木而肥墝之勢可知。」又曰:「稼穡不修,桑果不茂,畜產不肥,鞭之可也;杝(二六)落不完,垣牆不牢,掃除不淨,笞之可也「四四」。」此督課之方也。且天子親耕,皇后親蠶,況夫田父而懷窳惰乎?
李衡「四五」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,種甘橘千樹。臨死敕兒曰:「吾州里有千頭木奴,不責汝衣食,歲上一匹絹,亦可足用矣。」吳末,甘橘成,歲得絹數千匹。恒稱「四六」太史公所謂「江陵千樹橘,與千戶侯等」者也。樊重「四七」欲作器物,先種梓、漆,時人嗤之。然積以歲月,皆得其用,向之笑者,咸求假焉。此種殖(二七)之不可已已也。諺曰:「一年之計,莫如樹穀;十年之計,莫如樹木。」此之謂也。
《書》曰(二八):「稼穡之艱難。」《孝經》曰(二九):「用天之道,因地之利,謹身節用,以養父母。」《論語》曰(三十):「百姓不足,君孰與足?」漢文帝曰:「朕為天下守財矣,安敢妄用哉!」孔子曰(三一):「居家理,治可移於官。」然則家猶國,國猶家,是以家貧則思良妻,國亂則思良相,其義一也。
夫財貨之生,既艱難矣,用之又無節;凡人之性,好懶惰矣,率之又不篤;加以政令失所,水旱為災,一穀不登,胔腐(三二)相繼:古今同患,所不能止也,嗟乎!且飢者有過甚之願,渴者有兼量之情。既飽而後輕食,既暖而後輕衣。或由年穀豐穰,而忽於蓄積;或由布帛優贍,而輕於施與:窮窘之來,所由有漸。故《管子》曰(三三):「桀有天下,而用不足;湯有七十二里,而用有餘,天非獨為湯雨菽、粟也。」蓋言用之以節。
《仲長子》曰(三四):「鮑魚「四八」之肆,不自以氣為臭;四夷之人,不自以食為異:生習使之然也。居積習之中,見生然之事,夫孰自知非者也?斯何異蓼中之蟲,而不知藍之甘乎?」
今採捃經傳,爰及歌謠,詢之老成,驗之行事,起自耕農,終於醯、醢「四九」,資生之業,靡不畢書,號曰《齊民要術》。凡九十二篇,束(三五)為十卷。卷首皆有目錄,於文雖煩,尋覽差易。其有五穀、果、蓏非中國「五0」所殖者,存其名目而已;種蒔之法,蓋無聞焉。捨本逐末,賢哲所非,日富歲貧,飢寒之漸,故商賈之事,闕而不錄。花草之流,可以悅目,徒有春花,而無秋實,匹諸浮偽,蓋不足存。
鄙意曉示家童「五一」,未敢聞之有識,故丁寧周至,言提其耳,每事指斥,不尚浮辭。覽者無或嗤焉。
(一)見《史記‧平準書》,「蓋藏」作「藏蓋」。
(二)「若」,金抄作「若古」,「古」是衍文;明抄、湖湘本、《津逮》本又訛「若」為「者」,變成「者古」,不通;張校作「者若」。按《史記‧平準書》如淳注的原文是:「齊等無有貴賤,故謂之齊民,若今言平民矣。」張校多「者」字亦通,故從張校。
(三)注中三「民」字,原均作「人」,係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名改,宋以後一直沿用未改。《史記‧平準書》原文作「民」,茲據以改復。
(四)金抄、黃校、張校作「是」,明抄、湖湘本等作「食」。按本段全文係節引自《漢書‧食貨志》,此句《食貨志》原文是:「舜命后稷,以黎民祖飢,是為政首。」《要術》既刪去「以黎民祖飢」,應以明抄作「食」為長,故從明抄。
(五)見《管子‧揆度》篇,又見《輕重甲》篇,文字稍異。下面「倉廩實」云云,見《管子‧牧民》篇,二「知」字上均多「則」字。
(六)《論語‧微子》篇:「子路從(孔子)而後,遇丈人以杖荷蓧。子路問曰:「子見夫子乎?」丈人曰:「四體不勤,五穀不分,孰為夫子?」」
(七)見《左傳‧宣公》十二年,「人生」作「民生」。《要術》作「人」,可能也是唐人避改的。
(八)明抄、湖湘本無「古」字,金抄及《輯要》引有。
(九)「故李悝……而雄諸侯」,節採自《漢書‧食貨志》。《食貨志》原文是:「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,……國以富強。及秦孝公用商君,……急耕戰之賞,……傾鄰國而雄諸侯。」
(十)見《淮南子》(《四部叢刊》本)《脩務訓》,文字稍異。其中「陽盱」作「陽眄」,字書無「眄」字,疑誤。
(十一)《隋書‧經籍志》著錄有《仲長子昌言》十二卷。《昌言》係東漢仲長統撰,現已失傳。《後漢書‧仲長統傳》採錄其《昌言》中《理亂》等三篇,是極小一部分。唐‧魏徵等《群書治要》中收有「《仲長子昌言》」,與崔寔《政論》合成一卷,亦極簡略。《要術》所引仲長統各條,均不見此二書所採錄。其引文引到哪裏為止,只能主觀地就文義推斷。
(十二)《譙子》,或出三國蜀譙周,或出他人。書已佚。
(十三)各本均作「有」,《輯要》引作「無」。「不織不衣」,循下句例應作「不織則不衣」解釋,不作「可以不織不衣」解釋,則此處應作「無」。
(十四)晁錯語節引自《漢書‧食貨志》,文字無甚差別。
(十五)劉陶語見《後漢書‧劉陶傳》,文同。
(十六)陳思王即曹植(子建)。今傳《曹子建集》,已非完帙,不載此段語句。《藝文類聚》卷五「寒」引曹植所上表中有此記載,文句稍異,並有脫文。
(十七)金抄、明抄作「嘗更」;黃校作「常更」,「常」應作「嘗」;湖湘本、《津逮》本等作「常耕」,訛。宋陸佃《埤雅》卷五「羝」引《要術》(雖未標明,實出《要術》)作「更嘗」,陸游《感舊》詩自注引《要術》亦作「更嘗」,証明金抄的正確。因「湯」屬陽韻,「更」屬庚韻,古韻陽、庚同部,故湯、更相協,正合古諺形式。後世湯、嘗相協,乃倒「嘗更」為「更嘗」。
(十八)黃校、張校、明抄作「」,無此字,誤;金抄、湖湘本作「牸」,《孔叢子》原文亦作「牸」,音字,是母畜的通稱,茲據改。
(十九)明抄、湖湘本作「孿」,是雙生子,誤;金抄、《津逮》本等及《三國志‧魏志》引《魏略》均作「孿」,指裙的過分褶疊費料,茲據改。
(二十)「積」,金抄、明抄作「種」,誤;據湖湘本等及《後漢書‧崔寔傳》改正。
(二一)「潁」,明抄、湖湘本等作「穎」,誤;據金抄、漸西本及《漢書‧黃霸傳》改正。
(二二)金抄、黃校、張校作「樹」,同《漢書‧龔遂傳》;明抄、湖湘本等作「株」。
(二三)金抄及《輯要》引《要術》作「五雞」,他本作「五母雞」。按《要術》文句全同《漢書‧龔遂傳》,《龔遂傳》亦無「母」字,故從金抄。
(二四)金抄、黃校、明抄作「僮种」,張校作「童种」,湖湘本、《津逮》本等作「童恢」。茲從金抄,參看注釋〔三四〕。
(二五)明抄誤作「」,據金抄、湖湘本等及《魏志‧杜畿傳》改正。
(二六)各本均作「柂」,訛。《說文》:「杝,落也。」《通俗文》:「柴垣曰杝。」即籬笆。音豸,又音移。段玉裁注《說文》:「《齊民要術》引《仲長子》曰:「柂落不完,……」柂者,杝之誤。」茲據改。
(二七)明抄作「植」,茲依金抄作「殖」。
(二八)見《尚書‧無逸》篇。
(二九)見《孝經‧庶人章》,「因」作「分」。按此字有今、古文之異,今文作「分」,古文作「因」。《要術》採用古文。今本《孝經》為李隆基(唐玄宗)注本,採用今文作「分」。
(三十)見《論語‧顏淵》篇。
(三一)孔子語出《孝經‧廣揚名章》,「治」上多「故」字。此「故」字湖湘本等有,金抄、黃校、明抄無。《孝經》邢昺疏:「先儒以為「居家理」下闕一「故」字,御注加之。」「御注」即李隆基注。可見此字原來沒有,始加於唐。湖湘本等據加,非。
(三二)金抄、黃校、張校作「履」,明抄、湖湘本等作「腐」。按「胔」音疵,指屍體腐爛,與「腐」為複詞,自可解釋。「履」是步履,「胔履相繼」,雖可解釋為腐屍如步履之相繼,接踵而來,如《新唐書‧李栖筠傳》所謂「死徙踵路」,亦即卷二《種芋》篇「餓死滿道,白骨交橫」的意思,但以作「腐」較明允,故從明抄。
(三三)《管子》卷二三《地數》篇:「昔者桀霸有天下,而用不足;湯有七十里之薄,而用有餘,天非獨為湯雨菽、粟,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。」
(三四)《仲長子》語,不見今傳仲長統《昌言》,已在校記(十一)說明。此段語句,究竟至何處止為《仲長子》原文,很難確定。現在暫將全段作為《仲長子》原文。
(三五)金抄作「束」,他本作「分」。當時寫書捲束成「卷」,故從金抄。
「一」《漢書‧食貨志》:「堯命四子,以敬授民時。」四子指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,後亦簡稱羲和。事出《尚書‧堯典》,記載堯命四人釐定春夏秋冬四時,以正農時。
「二」《漢書‧食貨志》:「禹平洪水,定九州,制土田,……萬國作乂。」事出《禹貢》。「乂」是治理的意思。
「三」「祭」通「際」,不是祭祀。「桑林之祭」,《淮南子‧脩務訓》作「桑山之林」,而《主術訓》逕作「桑林之際」。又《本經訓》:「禽(即擒字)封狶(大豬)於桑林。」高誘注:「桑林,湯所禱旱「桑山之林」。」故「桑林之祭」,意即桑山之林際。《春秋繁露》卷十六《祭義》:「祭之為言,際也。」《廣雅‧釋言》:「祭,際也。」上文「以身解於陽盱之河」,《淮南子》高誘注:「為治水解禱,以身為質。解讀解除之解。」謂以身為質,為解除洪水災害祈禱,也就是決心要把洪水治好,不惜捐軀獻身之意。陽盱河,高注:「在秦地。」盱音吁。
「四」「求贍」,需要得到滿足,生活過得好。
「五」高誘注:「烈,業也。」
「六」「簠、簋」,古時盛食物的器具,竹木製或銅製。簠,音甫,外方內圓;簋,音軌,外圓內方。但型製亦有小異者。
「七」「釜」、「鍾」,古時量器名稱。釜是六斗四升,鍾是六石四斗。《左傳‧昭公三年》:「齊舊四量:豆、區、釜、鍾。四升為豆,各自其四,以登於釜,釜十則鍾。」
「八」「尚」,僥倖妄想的意思。《漢書‧敘傳上》:「尚粵其義。」顏師古注:「尚,庶幾也,願也。」《詩經‧衛風‧兔爰》孔穎達疏:「易曰:庶,幸也;幾,覬也。是庶幾者,幸覬之意也。」上文「矧夫」是何況的意思。
「九」「異宿」,指歇宿時有遠近,因為走得快的已趕到前站,走得慢的還掉在後頭,這是對下一句作比喻。
「一0」「短褐」,粗麻短衣。
「一一」趙過,漢武帝時任「搜粟都尉」(中央高級農官),曾總結農民經驗創製成一種「三犁共一牛」的新農具(即今耬車),見卷一《耕田》篇引崔寔《政論》文。他教導和推廣「代田法」和這種新農具的事蹟與成效《漢書‧食貨志》有詳細記述(卷一《種穀》篇引載其全文)。但牛耕不始於趙過,趙過只是在原已用牛耕的基礎上有所改進。
「一二」「縑」是細絹,「牘」是竹木簡,有紙以前的文字,寫在這些上面,即所謂「竹、帛」。其缺點是縑帛貴,竹、木簡笨重。「方」是「比」的意思。這是說自東漢蔡倫用植物纖維改進造紙方法後,比起過去來,就沒有用「縑、牘」那樣煩費了。事見《後漢書‧蔡倫傳》。
「一三」西漢宣帝時,耿壽昌建議在邊郡修建倉庫,穀賤時以較高的價格買進,貴時以較低的價格賣出,以調節糧價,叫做「常平倉」。事見《漢書‧食貨志》。
「一四」桑弘羊的「均輸法」,在經過試辦階段後,於漢武帝元封元年(公元前一一○年)正式施行於全國。辦法是把各地一向為商人所爭購販運牟利的產品,列為人民向政府繳納的實物貢賦(即將原徵貢賦的品類改變),由政府直接徵收掌握,除一部分按需要逕運京都長安外,其餘都由當地轉運到市價較高的地方賣去,把錢交回中央。這就是所謂「均輸」。主要目的在平抑物價,防止商人投機倒把,而增加中央收入。事見《史記‧平準書》及《漢書‧食貨志》。
「一五」「嘗」是曾經,「更」是經歷。這句古語是說,即使聰明如禹湯,終不如親身實踐得來的知識高明。
「一六」樊遲,孔子弟子,事見《論語‧子路》篇。
「一七」猗頓,春秋時人,在猗氏(今山西臨猗縣,一說安澤縣)牧養牛羊致富。事出《孔叢子》卷五《陳士義》篇,有較詳記載。所載陶朱公(即范蠡)語作:「子欲速富,當畜五牸。」《要術》卷六《養牛馬驢騾》篇再引此句同《孔叢子》。「五牸」,據《養牛馬驢騾》篇注文,指牛、馬、豬、羊、驢五種母畜。《史記‧貨殖列傳》及《漢書‧食貨志》均稱猗頓以鹽業致富,無繁殖牛羊致富說法。
「一八」任延,自漢光武初年至漢明帝永平十一年(公元六十八年)病卒,歷任九真、武威、潁川、河內四郡太守。在九真四年。事見《後漢書》及《東觀漢記‧任延傳》。「乃令鑄作田器,教之墾闢,歲歲開廣,百姓充給」一段文字,見於《後漢書‧任延傳》,指任延。王景事蹟,與此相類,故《要術》連類並稱,參看注釋「一九」。三百年後俞益期遷居其地,記述自任延教導犁耕以來,有「白田」、「赤田」的兩熟稻,「米不外散,恒為豐國」(參看卷十「稻〔二〕」注釋「一」)。
「一九」王景是東漢著名水利專家,治理黃河,著有功績。《後漢書‧王景傳》稱景於漢章帝建初八年(公元八十三年)任廬江太守,「先是,百姓不知牛耕,致地力有餘,而食常不足。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,景乃驅率吏民,修起蕪廢,教用犁耕。由是墾闢倍多,境內豐給。」芍陂是我國最早的大型蓄水陂塘,「陂徑百里,灌田萬頃」(王景傳李賢注)。今安徽壽縣安豐塘是其遺址,但已淤縮很多。廬江郡治在今安徽廬江縣。
「二0」皇甫隆,三國魏時人,嘉平(公元二四九至二五三年)中任燉煌太守。《三國志‧魏志》卷十六《倉慈傳》注引《魏略》稱:「初,燉煌不甚曉田,常灌溉滀水,使極濡洽,然後乃耕。又不曉作耬犁、用水。及種,人牛功力既費,而收穀更少。隆到,教作耬犁,又教衍溉。歲終率計,其所省庸力過半,得穀加五。」下文接敘節省裙料一事,《要術》文句,全同《魏略》。「耬犁」即耬車。皇甫隆不僅向燉煌地區傳進播種器,並且還改進了耕作和灌溉技術,所以得到增產。
「二一」茨充,漢光武時繼衛颯任桂陽太守,事蹟見《東觀漢記》及《後漢書‧茨充傳》,前者較詳,後者簡略。《要術》說茨充任桂陽縣令,與本傳不同。核對《要術》材料來源,似出《東觀漢記》,如非《漢記》有殘闕,疑即《要術》有誤字。桂陽郡治,在今湖南郴縣。桂陽縣即今廣東連縣。「今江南知桑蠶織履,皆充之教也。」《東觀漢記》原有,非《要術》所加,原文是:「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,皆充之化也。」因此「今」指《茨充傳》寫作的時代,不是賈思勰時代。
「二二」崔鴻《十六國春秋》:「王延,後母遇之無道,恒取鋪穰及敗麻頭,與延貯衣。」這裏「以麻枲頭貯衣」,當時沒有棉花,當地又不知養蠶,用廢麻頭裝進夾衣中取暖。「枲」音喜,大麻雄株。「麻枲頭」是緝績麻縷過程中剔剩下來的雜亂麻纖維,也叫「麻腳」。
「二三」「麤」是南楚人稱麻鞋草履的俗名,這裏不是「粗」的異寫字。揚雄《方言》卷四:「屝、屨、麤、履也。……南楚、江、沔之間,總謂之麤。」史游《急就篇》顏師古注:「麤者,麻枲雜履之名也,南楚、江、淮之間,通謂之麤。」字亦作「●」,《釋名‧釋衣服》:「荊州人曰●,絲、麻、韋、草,皆同名也。●,措也,言所以安措足也。」《說文》:「●,艸履也。」清桂馥《說文解字義證》即引《東觀漢記》「少麤履」此句以證釋說文「●」字。桂陽地屬南楚,茨充正用了當地的方言,《茨充傳》是根據茨充的材料寫的。上文「窳」,音羽,懶的意思。
「二四」「紵麻」即苧麻。
「二五」崔寔,東漢後期漢桓帝時人,著有《四民月令》和《政論》。二書均已失傳,《要術》各篇均有引到,特別是《四民月令》,由於《要術》的引錄,最早保存了大量的資料。崔寔事蹟見《後漢書‧崔寔傳》。五原郡大致包括今內蒙古自治區五原、臨河及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西部地區。
「二六」黃霸,漢武帝末年做過「均輸長」,漢宣帝時二次出任潁川太守,先後八年。後累遷至丞相。《要術》所述事蹟,節引自《漢書‧黃霸傳》。潁川郡治在今河南禹縣。
「二七」據《漢書‧黃霸傳》顏師古注,「郵亭」指傳送文書的止歇站(即驛站),「鄉官」指鄉政府辦事處,當然也包括其基層小吏,即所謂「三老」(掌教化)、「嗇夫」(掌賦稅、訴訟)、「游徼」(掌治安)。下文「鄉部」,即指鄉辦事處。
「二八」龔遂,漢宣帝時年七十餘,初任渤海太守。《要術》所述事蹟,出自《漢書‧龔遂傳》。渤海郡約有今河北省濱海地區。龔遂、黃霸,世稱「良吏」,文獻上往往「龔黃」並稱。
「二九」「」即「薤」字。
「三0」「課」,指檢查考核其收獲多少,是否達到預期的標準?下文「督課」則指督促與課罰。
「三一」召信臣,稍後於龔遂,曾任零陵、南陽、河南三郡太守,漢元帝竟寧元年(公元前三十三年)徵為少府。《要術》所述,節引自《漢書召信臣傳》。南陽郡有今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北部偏西地區。
「三二」「鄉亭」是漢代縣以下的行政區劃單位,即所謂「十里一亭,十亭一鄉」。(《漢書‧百官公卿表》)《易經‧序卦》:「離者,麗也。《說文》:「麗,旅行也。」《詩經‧小雅‧魚麗》毛《傳》:「麗,歷也。」是「離」即經歷之意。《要術》語出《漢書》,《漢書‧西域傳上》「離一二旬」,顏師古注:「離,亦歷也。」證明「離鄉亭」意即「歷鄉亭」,不是離開鄉亭。此句意謂召信臣進入農村,隨在止宿,其止宿之處,經歷各鄉各亭,很少呆在太守衙門里。
「三三」「水門」即水閘。「閼」音遏,作「堰」字用。《漢書》顏師古注:「所以壅水。」周壽昌《漢書注校補》:「提即隄字。」《漢書補注》引錢大昕:「提閼即堤堰。」
「三四」范曄《後漢書‧童恢傳》李賢注稱,童恢,謝承《後漢書》作「僮种」。據此,僮种即童恢,《要術》材料,似根據謝承《後漢書》。但《要術》所敘僮种事蹟,范曄《後漢書‧童恢傳》不載。謝承《後漢書》已失傳,現在殘存的《東觀漢記》亦無僮种或童恢傳記。二人關係究竟如何,已無從查證。不其縣在今山東即墨縣。
「三五」《三國志‧魏志‧倉慈傳》:「京兆太守濟北顏斐,……為良二千石。」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:「顏斐,字文林。……黃初(公元二二○至二二六年)初,轉為黃門侍郎,後為京兆太守。始京兆從馬超破後,民人多不專於農殖。又歷數四二千石,取解目前,亦不為民作久遠計。斐到官,乃令屬縣整阡陌,樹桑果,……。」下文與《要術》所記相同。但《要術》作「顏裴」,丁國鈞《校勘記》:「以其字文林推之,此「裴」字當為「斐」之訛」,茲據《魏略》改作「斐」。漢代的京兆尹,魏改稱京兆郡,郡治在今西安附近。
「三六」「匠」指製車技藝。
「三七」「丁」,堅實的意思。
「三八」王丹,東漢初人,《後漢書》及《東觀漢記》均有傳。下文「」,同「懶」。
「三九」杜畿,東漢末魏初人,任河東太守十六年。《三國志‧魏志》有傳。《要術》所敘,與《魏志》相同。河東郡在今山西省西南隅。
「四0」「草馬」即母馬。
「四一」《詩經‧小雅‧甫田》:「曾孫之庾,如坻如京。」廩積為倉,露積為庾。京、坻皆有高丘之義,這裏是說穀物堆積得象高丘那樣,形容很多。
「四二」「堀」通「窟」。
「四三」「鄭」,指秦王政(即秦始皇)元年(公元前二四六年)韓國水利專家鄭國主持開鑿的鄭國渠;「白」,指漢武帝太始二年(公元前九十五年)白公主持修鑿的白渠。二渠均引涇水灌溉,使關中農產獲得豐收。
「四四」仲長統時期封建莊園在形成中,大小莊園主役使著大量的和不少的「奴客」,這裏用鞭打、杖揍的辦法對付他們,充分暴露莊園主對男女「奴客」的殘酷。
「四五」李衡,三國時仕於吳,後出任丹楊太守。《吳志‧孫休傳》裴松之注引《襄陽記》:「李衡,……漢末入吳。……後嘗為諸葛恪司馬。……恪被誅,求為丹陽太守。……衡每欲治家,妻輒不聽。後密遣客(按指「佃客」、「奴客」)十人,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,種甘橘千株。臨死敕兒曰:「汝母惡吾治家,故窮如是。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,不責汝衣食,歲上一匹絹,亦可足用耳。」……吳末,衡甘橘成,歲得絹數千匹,家道殷足。晉咸康(公元三三五-三四二年)中,其宅上枯樹猶在。」《水經注》卷二七「沅水」並載其事:「沅水又東歷龍陽縣之氾洲。洲長二十里,吳丹楊太守李衡植柑於其上。」武陵郡的龍陽縣,吳置,在今湖南漢壽縣,地當沅江入洞庭湖處。「氾」同「汎」,「汎洲」指湖中大片的淤積洲。「甘」即「柑」字。又東晉習鑿齒《襄陽耆舊傳》亦載其事,但說「漢末為丹陽太守」。李衡妻是習竺之女,與習鑿齒同族。
「四六」「恒稱」云云,是李衡自己常說的話。李衡死後,其子將千樹柑橘的話告知母親。其母從七八年前忽然不見了十戶「奴客」和李衡常說的話聯係起來推測,纔知道有在龍陽營植柑園的事。這常說的話就是:「汝父恒稱太史公言:「江陵千樹橘,當封君家。」」上一注釋所引《襄陽記》等三項資料均有是項記載。太史公語見《史記‧貨殖列傳》。
「四七」樊重,漢光武劉秀的外祖。《要術》所述,見《後漢書‧樊重傳》,文句全同。
「四八」「鮑魚」,即醃魚,不是鰒魚(石決明)。《釋名‧釋飲食》:「鮑魚,鮑,腐也,埋藏奄使腐臭也。」「奄」即「醃」字。參看卷七《貨殖》篇「鮿、鮑千鈞」顏師古注。
「四九」「醯」音兮,原義是酸,這裏包括《要術》製醋、作菹和釀造各法。「醢」音海,原義是肉醬,引申為「烹」,這裏包括各種醬、豉和醬藏食物以及腌臘、烹調各法。
「五0」「中國」,指我國北方(主要是後魏的疆域)。
「五一」「家童」,指「家客」、「奴客」,不是賈家的年輕子弟。《說文》●部:「童,男有(按即罪字)曰奴,奴曰童。」說明「童」指奴隸。而童子的童,古作「僮」,《說文》:「僮,未冠也。」卷五《種紅藍花梔子》篇正稱「小兒僮女」。和賈思勰同時稍後的顏之推則亦稱「奴客」為「家童」,如《顏氏家訓‧治家》篇:「家童八百,誓滿一千。」盧文弨解釋說:「古僮僕作「童」,童子作「僮」;後乃互易。」《要術》卷三《蕪菁》篇:「三載得一奴」,「二十載得一婢」,卷七《造神麴并酒》篇有「奴客」,這些都包括在當時所謂「家童」的範圍之內。
- 下一篇: ▪ 文 ▪ 贾思勰 - 杂说
- 上一篇: ▪ 文 ▪ 李筌 - 跋·跋